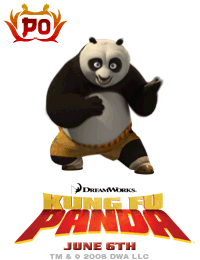5月9日 那曲——格爾木 832公里
一早6:30出發,到8:15到了安多,安多海拔4500米,藏區的最后一個城鎮,藏語意思為“尾部或下部”。安多條件非常差,我們吃了早飯。安多就是西藏與青海的交界了,生活著安多藏族。然后進入西藏羌塘高原,因走得太早,我一路都迷迷糊糊地睡著。經過了雁石坪。


翻越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大氣含氧量僅60%)時我們幾乎都沒有什么反應,因為只要趕路,我們每天幾乎都要翻越幾座4000多米的山口,而且已經翻過5008米的東達山。唐古拉山脈最高峰為格拉丹東峰,海拔6621米。300年前,牧民冬巴.果切帶著家眷,趕著牛羊,跋山涉水,從唐古拉南側來此雪山安了家,并發展成為一個強盛的部落——安多多瑪部落。后來,冬巴.果切請來了一位法力無邊的活佛為這座壯麗的雪山開光,并將此山命名為“嘎爾.格拉丹東”,意為“哈達質的矛形佛身”。從此,格拉丹東便成為藏北群山之首領,安多多瑪部落奉它為神山。格拉丹東峰西南最大的山谷冰川——姜谷迪如冰川,是長江的發源地,冰川融水匯成了長江源流正源沱沱河。“而位于格拉丹東東北部的崗加曲巴冰川,其融水則匯成尕日曲(尕爾曲),尕日曲匯同更多的支流構成長江南源當曲,并與沱沱河一并融合貫通成為通天河。




通天河源源東去,穿越長江第一大峽谷“煙瘴掛峽谷”,在曲麻萊縣境又與發源于可可西里腹地的長江北源楚瑪爾河匯流,從此,通天河一路穿峽越谷,蕩氣回腸,綿延800公里。在康巴世襲居住的玉樹草原接納巴塘河,一并流入四川省境內,百折不回的通天河搖身間變成了金沙江,之后揚子江,最后是被稱為泱泱大中華龍脈的長江。
長江源流正是由正源沱沱河,南源當曲,北源楚瑪爾河這三條主要水源共同構架了龐大的扇形水系,在這片面積約14萬平方公里廣袤的區域邊緣,南有巍峨唐古拉,北有蒼茫昆侖山,兩山寬400余公里,間架舒緩的可可西里山。在這片平均海拔近5000米的茫茫荒原上生活著眾多高原珍稀野生動物。”
我們過了長江源頭第一橋,沱沱河大橋。沱沱河幾乎都干了,它全長370公里,上游的自然條件十分惡劣。
翻越唐古拉山口后我們應該就進入了青海。一路都在趕路呀,還經過了二道溝、風火山口(海拔5010米),風火山帶些褚紅色,據說黃昏時是一片近似火紅色的山群,有些像吐魯番的火焰山。
隨后到五道梁,它的空氣含氧量僅有平原含氧量的40%,是青藏線上的“鬼門關”。整個地貌可以說是不毛之地,黃土,幾乎干涸的河流,只有零零星星的幾叢干枯的雜草。又經過楚瑪爾河(發源于可可西里山)、索南達杰保護站,從這里可以進入可可西里無人區,不凍泉,昆侖山口(海拔4767米)。昆侖山脈、唐古拉山脈、念青唐古拉山脈把海洋來的水汽都擋住了,我們覺得干燥極了。這里是東昆侖區域,距離格爾木110公里左右時,我們在西大灘看到了玉珠峰和它的三條冰川。玉珠峰海拔6178米,是比較好攀登的一座山,許多初級登山者會選擇它。但2000年這里遇難了5個人。還有玉虛峰(5980米)。最后經過納赤臺(藏語為“沼澤中的臺地”)。






我們原本希望能趕到都蘭(離格爾木350公里),但后來一到格爾木,大家本來說只是吃碗面,一吃上就走不動了。我們就住在水利賓館。
明天就不去鳥島了,會經過青海湖,最后住在西寧,全程也將有800多公里。
5月10日 格爾木——西寧
路太好了,我們清晨近9:00出發,下午5:20就到了西寧。
中途看到一些小型的龍卷風地帶,非常有趣。

先到了都蘭,徑直往前開,一直到黑馬河,看見遼闊的青海湖,沿環湖公路自西向東,到達倒淌河(據西寧96公里),再走兩段一級公路,到達西寧。
青海湖蒙語叫“庫庫諾爾”,藏語叫“溫布措”,意思是“青色的海”,青海由此得名。青海湖海拔3260米。
青海湖極為遼闊,湛藍的湖水就像大海一樣,這里的人們都稱它為海。湖邊有成群的牛羊,還有雁鷗漫步和展翅。往遠處望,一座小島模糊可見,叫做海心山。



晚上受到田總表哥、表弟的熱烈歡迎和頻繁的敬酒。不過吃到了非常正宗的釀皮,青稞做的酒釀,晚上又喝到了非常稠、非常酸、味道極濃郁,天下美味西寧酸奶。
最后,我們去看了塔爾寺,塔爾寺又名塔兒寺。得名于大金瓦寺內為紀念黃教創始人宗喀巴而建的大銀塔,藏語稱為“袞本賢巴林”,意思是:“十萬獅子吼佛像的彌勒寺”。它座落在湟中縣魯沙爾鎮西南隅的蓮花山坳(相當于一盆地)中,是我國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六大寺院之一。塔爾寺諸佛殿裝飾的堆繡、壁畫和酥油花,被人們稱為藝術“三絕”,其中尤以酥油花最為有名。(可惜我們不能拍攝酥油花)。酥油花相傳是當年文成公主和松贊干布聯姻時,當地佛教徒為表示尊敬,讓公主從長安出發時帶來的,一尊佛像前供奉一束酥油花,逐漸在西藏成為習俗,后來傳到塔爾寺。




塔爾寺是宗喀巴大師羅桑扎巴(1357-1419)的誕生地。宗喀巴大師早年學經于夏瓊寺,16歲去西藏深造,改革西藏佛教,創立格魯派(黃教),成為一代宗師。傳說他誕生以后,從剪臍帶滴血的地方長出一株白旃檀樹,樹上十萬片葉子,每片上自燃顯現出一尊獅子吼佛像(釋迦牟尼身像的一種),“袞本” (十萬身像)的名稱即源于此。
宗喀巴去西藏6年后,其母香薩阿切盼兒心切,讓人捎去一束白發和一封信,要宗喀巴回家一晤。宗喀巴接信后,為學佛教而決意不返,給母親和姐姐各捎去自畫像和獅子吼佛像1幅,并寫信說:“若能在我出生的地點用十萬獅子吼佛像和菩提樹(指宗喀巴出生處的那株白旃檀樹)為胎藏修建一座佛塔,就如與我見面一樣”。第二年,即明洪武十二年(1379),香薩阿切在信徒們的支持下建塔,取名“蓮聚塔”。后來發展成現在的塔爾寺。
 引用
刪除
piaoliang110mei / 2007-10-30 11:19:06
引用
刪除
piaoliang110mei / 2007-10-30 11:1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