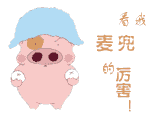近十年來,由于北京人口堆積,進京的水只能保證生活使用,于是就從農業、生態、工業那奪水,城市里的生態用水異常緊缺。北京雖然也在治污,但治理完的污水仍舊骯臟無比,治理完的污水處于北京的下游,無法回到上游。這樣,像北大這樣位于“上風上水”之地,只好讓湖泊干涸。
能解決的似乎是利用雨水,而北大在這方面無所作為,于是雨水這邊成為城市的災難,那邊又無法滋潤干涸的湖底。
北大不是全國湖泊最多的大學,也不是湖泊面積最大的大學,但可能是湖泊對師生影響最大的大學,湖泊讓校園詩意彌漫的大學。未名湖所代表的隨時代波動精神,后湖、紅湖所代表的自由散漫精神,似乎都是這個大學多少還存在一點知識分子氣息的元氣所在。
然而北大似乎仍舊不知道大學為何物,一心只想蓋高樓,鋪路面。一邊既拿著國立北京大學的撥款,一邊又向社會募集資金。發動校友捐款之類也就罷了,有時候又難免想經營起企業來。等于是社會所有獲取利益的方式都干,唯獨不做大學最應當做的事。
公眾期望的大學,大體有三大作為。一是獨立研究,自由思考。這樣才可能替人類打破諸多的籓籬,從某些看似不可能之處進入高尚之地。二是自由表達,積極應世,這樣知識才可能對時事有所應答,知識分子才可能才時事有所助益。三是傳承思想,傳播學問,這樣才可能生生不息,光彩斐然。
一個只知道蓋大樓的大學顯然不是真大學,一個只知道爭評教授、爭取項目的大學也不是真大學。一個只知道拼命地招生卻無法讓學生“化平庸為神奇”大學,也不是一所真正的大學。一個對校園生態系統無力保護的大學不是真大學,一個對校園文物價值無力繁衍的大學也不是真大學,一個對校園學生多樣性無力激發的大學也不是真大學。
北大的后湖和紅湖,大概在幾年前就沒水供養了。他們在過去都是有水的,周邊天然植物隨意生長,自然天成,自由自在,深得明清時期海淀園林的真脈。北京不再分配足夠的生態用水之后,北大就只能聽任這些湖泊一天天干涸和萎縮下去。無論你在夏天還是在冬天,你到這些湖面邊去看,你看到的分明就是一個個干癟的青春,它們過早地被命運送給了只會制造衰亡的病魔。
沒水就沒水吧,至少在春天來臨的時候,鴛鴦和綠頭鴨、鵲鴨還會選擇這里繁殖。至少在夏天雨水多的時候,你還能看到湖里的殘荷與慈菇在掙扎著生長。至少在秋風甚緊的時候,你在湖邊小道上漫步,還得吸得一點自然的真意。至少在冬日的深夜,你在湖底僵臥的干雪上面,還能找到一點人文精神的夢想。
然而北大的校方似乎喜歡這樣的干涸。湖里有水的時候,想要抽干它、填掉它,不要說水里的各種生物不樂意,就是學校里的師生,學校外的閑人,也都對此分外的敏感。可能抽水機剛剛放下,那邊就已經有人開始鬧將起來。
這樣的干涸讓校方充滿了無辜感。他們覺得十幾個小湖的干涸見底、干渴待斃不是他們的責任。聰明的人,可推之為天災,因為北京近年降水日益稀少,由于全球氣候變化。更聰明的人,可以推給城市管理者,是他們硬著心腸不給北大配給應得的水分。就是沒想過,自己有沒有辦法自救。
而湖底的“自然干涸”甚至是讓校方欣喜的。干涸的湖底分明就是上好的建筑用地。淤積的底泥讓濕地在緩慢地生長為“地基”。于是,在自然界這樣有心的配合下,北大校方完全可以借蓋國際數學中心、人文樓群的機會,把各種小湖填掉,讓其成為地下之鬼。
好在北大有那么幾個好事之徒,像聞丞、王放,這幾年一直在做北大后湖生態系統的調查。他們緩慢而堅定地揭示了“北大的秘密”,他們發現北大后湖里生長著至少種北京本地魚類,他們察覺北大是全國高校中少有的鴛鴦與綠頭鴨的繁殖地,他們記錄了鯰魚在后湖交配時的盛況,他們驚喜地發現紅隼在這些湖邊的建筑隱秘處繁殖后代,他們也發現了栓皮櫟讓雄鴛鴦羽毛豐采照人的秘訣。他們知道
2010年孵化的一窩5小綠頭鴨與它們的父母一起成了建筑工人的下酒菜;他們發現2010年孵出的一窩11只小綠頭鴨最后只有1只長到了亞成,其余的不是被流浪貓抓走就是讓未名湖的肉食動物所享用。
能夠保持北大顏面的似乎只有未名湖,而未名湖的命運本來是與后湖高度關聯的。而今,北大像保護嫡生長子一樣通過抽取深層地下水來保證未名湖的穩定,而對后湖和紅湖,北大則將其像私生子一樣拋棄給“市場開發”。
讓人好笑的是,填湖、砍樹、挖山,北大大費周章要蓋的建筑,一是國際數學中心,二是包括中文、歷史、哲學在內的“人文樓群”。不知道這些院系的學者和學生們,踏著湖泊的尸體大談精神和理想的時候,對已經衰亡的生態系統,對逝去的魚類和鳥類,作何感想?
未名湖估計也命運不濟,如果北京繼續漠視生態用水對于社會的意義,如果北大繼續狂喜地迎接干涸見“地”時代的到來,那么北大校園被填充為建筑樓群密布的
“世界一流大學”,是早晚的事。最終,填掉未名湖,拔掉博雅塔,砍去所有的天然樹,除去所有的天然草,讓學生像流水線上的產品一樣按照標準化生產,讓教授們像聽話的牛羊一樣每天到奶站定時交奶,是必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