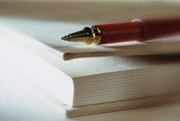【轉帖】楊絳:《走到人生邊上》 序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8-31 22:45:26/ 個人分類:精品美文
楊絳:《走到人生邊上》 序
我已經走到人生的邊緣邊緣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沒有了”。中外一例,都用這種種詞兒軟化那個不受歡迎而無可避免的“死”字。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規律,誰也逃不過。雖說:“老即是病”,老人免不了還要生另外的病。能無疾而終,就是天大的幸運;或者病得干脆利索,一病就死,也都稱好福氣。活著的人盡管舍不得病人死,但病人死了總說“解脫了”。解脫的是誰呢?總不能說是病人的遺體吧?這個遺體也決不會走,得別人來抬,別人來埋。活著的人都祝愿死者“走好”。人都死了,誰還走呢?遺體以外還有誰呢?換句話說,我死了是我擺脫了遺體?還能走?怎么走好?走哪里去?
我想不明白。我對想不明白的事,往往就擱下不想了。可是我已經走到了人生邊上,自己想不明白,就想問問人,而我可以問的人都已經走了。這類問題,只在內心深處自己問自己,一般是不公開討論的。我有意無意,探問了近旁幾位七十上下的朋友。朋友有親有疏,疏的只略一探問。
沒想到他們的回答很一致,很肯定,都說人死了就是沒有了,什么都沒有了。雖然各人說法不同,口氣不同,他們對自己的見解都同樣堅信不疑。他們都頭腦清楚,都是先進知識分子。我提的問題,他們看來壓根兒不成問題。他們的見解,我簡約地總結如下:
“老皇歷了!以前還要做水陸道場超度亡靈呢!子子孫孫還要祭祀‘作饗’呢!現在誰還迷信這一套嗎?上帝已經死了。這種神神鬼鬼的話沒人相信了。人死留名,雁死留聲,人世間至多也只是留下些聲名罷了。”
“人死了,剩下一個臭皮囊,或埋或燒,反正只配肥田了。形體已經沒有了,生命還能存在嗎?常言道:‘人死燭滅’,蠟燭點完了,火也滅了,還剩什么呢?”
“人生一世,草生一秋。草黃了,枯了,死了。不過草有根,明年又長出來。人也一樣,下一代接替上一代,代代相傳吧。一個人能活幾輩子嗎?”
“上帝下崗了,現在是財神爺坐莊了。誰叫上帝和財神爺勢不兩立呢!上帝能和財神爺較量嗎?人活一輩子,沒錢行嗎?掙錢得有權有位。爭權奪位得靠錢。稱王稱霸只為錢。你是經濟大國,國際間才站得住。沒有錢,只有死路一條。咱們現在居然‘窮則變,變則通了’,知道最要緊的是理財。人生一世,無非掙錢、花錢、享受,死了能帶走嗎?”
“人死了就是沒有了,什么都沒有了。還有不死的靈魂嗎?我壓根兒沒有靈魂,我生出來就是活的,就得活到死,盡管活著沒意思,也無可奈何。反正好人總吃虧,壞人總占便宜。這個世界是沒有公道的,不講理的,可是有什么辦法呢,什么都不由自主呀。我生來是好人,沒本領做惡人,吃虧就吃虧吧。盡管做些能做的事,就算沒有白活了。”
“我們這一輩人,受盡委屈、吃盡苦楚了。從古以來,多少人‘搔首問青天’,可是‘青天’,它理你嗎?圣人以神道設教,‘愚民’又‘馭民’,我們不愿再受騙了。迷信是很方便的,也頂稱心。可是‘人民的鴉片’畢竟是麻醉劑呀,誰愿意做‘癮君子’呢?說什么‘上帝慈悲’,慈悲的上帝在干什么?他是不管事還是沒本領呀?這種昏聵無能的上帝,還不給看破了?上帝!哪有上帝?”
“我學的是科學。我只知道我學的這門學科。人死了到哪里去是形而上學,是哲學問題,和我無關。我只知道人死了就什么都沒有了。”
他們說話的口氣,比我的撮述較為委婉,卻也夠叫我慚愧的。老人糊涂了!但是我仔細想想,什么都不信,就保證不迷嗎?他們自信不迷,可是他們的見解,究竟迷不迷呢?
第一,比喻只是比喻。比喻只有助于表達一個意思,并不能判定事物的是非虛實。“人生一世,草生一秋”只借以說明人生短暫。我們也向人祝愿“如松之壽”、“壽比南山”等等,都只是比喻罷了。
“人死燭滅”或“油干燈燼”,都是用火比喻生命,油或脂等燃料比喻軀體。但另一個常用的比喻“薪盡火傳”也是把火比喻生命,把木柴比喻軀體。脂、油、木柴同是燃料,同樣比作軀體。但“薪盡火傳”卻是說明軀體消滅后,生命會附著另一個軀體繼續燃燒,恰恰表達靈魂可以不死。這就明確證實比喻不能用來判斷事物的真偽虛實。比喻不是論斷。
第二,名與實必須界說分明。老子所謂“名可名,非常名”。如果名與實的界說不明確,思想就混亂了。例如“我沒有靈魂”云云,是站不住的。人死了,靈魂是否存在是一個問題。活人有沒有靈魂,不是問題,只不過“靈魂”這個名稱沒有定規,可有不同的名稱。活著的人總有生命——不是蟲蟻的生命,不是禽獸的生命,而是人的生命,我們也稱“一條人命”。自稱沒有靈魂的人,決不肯說自己只有一條狗命。常言道:“人命大似天”或“人命關天”。人命至關重要,殺人一命,只能用自己的生命來抵償。“一條人命”和“一個靈魂”實質上有什么區別呢?英美人稱soul,古英文稱ghost,法國人稱?#092;\me,西班牙人稱alma,辭典上都譯作靈魂。靈魂不就是人的生命嗎?誰能沒有生命呢?
又例如“上帝”有眾多名稱。“上帝死了”,死的是哪一門子的上帝呢?各民族、各派別的宗教,都有自己的上帝,都把自己信奉的上帝稱真主,稱唯一的上帝,把異教的上帝稱邪神。有許多上帝有偶像,并且狀貌不同。也有沒有偶像的上帝。這許多既是真主,又是邪神,有偶像和無偶像的上帝,全都死了嗎?
人在急難中,痛苦中,煩惱中,都會喚天、求天、問天,中外一例。上帝應該有求必應,有問必答嗎?如果不應不答,就證明沒有上帝嗎?
耶穌受難前夕,在葡萄園里禱告了一整夜,求上帝免了他這番苦難,上帝答理了嗎?但耶穌失去他的信仰了嗎?
中國人絕大部分是居住農村的農民。他們的識見和城市里的先進知識分子距離很大。我曾下過鄉,也曾下過干校,和他們交過朋友,能了解他們的思想感情,也能認識他們的人品性格。他們中間,當然也有高明和愚昧的區別。一般說來,他們的確思想很落后。但他們都是在大自然中生活的。他們的經歷,先進的知識分子無緣經歷,不能一概斷為迷信。以下記錄的,都是篤實誠樸的農民所講述的親身經歷。
“我有夜眼,不愛使電棒,從年輕到現在六七十歲,慣走黑路。我個子小,力氣可大,啥也不怕。有一次,我碰上‘鬼打墻’了。忽然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見,只看到旁邊許多小道。你要走進這些小道,會走到河里去。這個我知道。我就發話了:‘不讓走了嗎?好,我就坐下。’我摸著一塊石頭就坐下了。我掏出煙袋,想抽兩口煙。可是火柴劃不亮,劃了十好幾根都不亮。碰上‘鬼打墻’,電棒也不亮的。我說:‘好,不讓走就不走,咱倆誰也不犯誰。’我就坐在那里。約莫坐了半個多時辰,那道黑墻忽然沒有了。前面的路,看得清清楚楚。我就回家了。碰到‘鬼打墻’就是不要亂跑。他看見你不理,沒辦法,只好退了。”
我認識一個二十多歲農村出生的女孩子。她曾讀過我記的《遇仙記》(參看《楊絳文集》第二卷228—233頁。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版),問我那是怎么回事。我說:“不知道,但都是實事。全宿舍的同學、老師都知道。我活到如今,從沒有像那夜睡得像死人一樣。”她說:“真的,有些事,說來很奇怪,我要不是親眼看見,我決不相信。我見過鬼附在人身上。這鬼死了兩三年了,死的時候四十歲。他的女兒和我同歲,也是同學。那年,挨著我家院墻北面住的女人剛做完絕育手術,身子很弱。這個男鬼就附在這女人身上,自己說:‘我是誰誰誰,我要見見我的家人,和他們說說話。’有人就去傳話了。他家的老婆、孩子都趕來了。這鬼流著眼淚和家里人說話,聲音全不像女人,很粗壯。我媽是村上的衛生員,當時還要為這女人打消炎針。我媽過來了,就掐那女人的上嘴唇——叫什么‘人中’ 吧?可是沒用。我媽硬著膽子給她打了消炎針。這鬼說:‘我沒讓你掐著,我溜了。嫂子,我今兒晚上要來嚇唬你!”我家晚上就聽得嘩啦啦的響,像大把沙子撒在墻上的響。響了兩次。我爹就罵了:‘深更半夜,鬧得人不得安寧,你王八蛋!’那鬼就不鬧了。我那時十幾歲,記得那鬼鬧了好幾天,不時地附在那女人身上。大約她身子健朗了,鬼才給趕走。”
在“餓死人的年代”,北京居民只知道“三年自然災害”。十年以后,我們下放干校,才知道不是天災。村民還不大敢說。多年后才聽到村里人說: “那時候餓死了不知多少人,村村都是死人多,活人少,陽氣壓不住陰氣,快要餓死的人往往夜里附上了鬼,又哭又說。其實他們只剩一口氣了,沒力氣說話了。可是附上了鬼,就又哭又說,都是新餓死的人,哭著訴苦。到天亮,附上鬼的人也多半死了。”
鬼附人身的傳說,我聽得多了,總不大相信。但仔細想想,我們常說:“又做師娘(巫婆)又做鬼”,如果從來沒有鬼附人身的事,就不會有冒充驅鬼的巫婆。所以我也相信莎士比亞的話:這個世界上,莫名其妙的事多著呢。
《左傳》也記載過鬧鬼的事。春秋戰國時,鄭國二貴胄爭權。一家姓良,一家姓駟。良家的伯有驕奢無道,駟家的子皙一樣驕奢,而且比伯有更強橫。子皙是老二,還有個弟弟名公孫段附和二哥。子皙和伯有各不相下。子皙就叫他手下的將官駟帶把伯有殺了。當時鄭國賢相子產安葬了伯有。子皙擅殺伯有是犯了死罪,但鄭
伯有死后化為厲鬼,六七年間經常出現。據《左傳》,“鄭人相驚伯有”,只要聽說“伯有至矣”,鄭國人就嚇得亂逃,又沒處可逃。伯有死了六年后的二月間,有人夢見伯有身披盔甲,揚言:“三月三日,我要殺駟帶。明年正月二十八日,我要殺公孫段。”那兩人如期而死。鄭國的人越加害怕了。子產忙為伯有平反,把他的兒子“立以為大夫,使有家廟”,伯有的鬼就不再出現了。
鄭子產出使晉國。晉國的官員問子產:“伯有猶能為厲乎?”(因為他死了好多年了。)子產曰:“能”。他說:老百姓橫死,鬼魂還能鬧,何況伯有是貴胄的子孫,比老百姓強橫。他安撫了伯有,他的鬼就不鬧了。
我們稱鬧鬼的宅子為兇宅。錢鍾書家曾租居無錫留芳聲巷一個大宅子,據說是兇宅。他叔叔夜晚讀書,看見一個鬼,就去打鬼,結果大病了一場。我家一九一九年從北京回無錫,為了找房子,也曾去看過那所兇宅。我記得爸爸對媽媽說:“兇宅未必有鬼,大概是房子陰暗,住了容易得病。”
但是我到過一個并不陰暗的兇宅。我上大學時,我和我的好友周芬有個同班女友是常熟人,家住常熟。一九三一年春假,她邀我們游常熟,在她家住幾天。我們同班有個男同學是常熟大地主,他家剛在城里蓋了新房子。我和周芬等到了常熟,他特來邀請我們三人過兩天到他新居吃飯,因為他媽媽從未見過大學女生,一定要見見,酒席都定好了,請務必賞光。我們無法推辭,只好同去赴宴。
新居是簇新的房子。陽光明亮,陳設富麗。他媽媽盛裝迎接。同席還有他爸爸和孿生的叔叔,相貌很相像;還有個瘦弱的嫂子帶著個淘氣的胖侄兒,還有個已經出嫁的妹妹。據說,那天他家正式搬入新居。那天想必是挑了“宜遷居”的黃道吉日,因為搬遷想必早已停當,不然的話,不會那么整潔。
回校后,不記得過了多久,我又遇見這個男同學。他和我們三人都不是同系。不常見面。他見了我第一事就告訴我他們家鬧鬼,鬧得很兇。嫂子死了,叔叔死了,父母病了,所以趕緊逃回鄉下去了。據說,那所房子的地基是公共體育場,沒知道原先是處決死囚的校場。我問:“鬼怎么鬧?”他說:“一到天黑,樓梯上腳步聲上上下下不斷,滿處咳吐吵罵聲,不知多少鬼呢!”我說:“你不是在家住過幾晚嗎?你也聽到了?”他說他只住了兩夜。他像他媽媽,睡得濃,只覺得城里不安靜,睡不穩。春假完了就回校了。鬧鬼是他嫂子聽到的,先還不敢說。他叔叔也聽到了。嫂子病了兩天,也沒發燒,無緣無故地死了。才過兩天,叔叔也死了,他爹也聽到鬧,父母都病了。他家用男女兩個傭人,男的管燒飯,是老家帶出來的,女的是城里雇的。女的住樓上,男的住樓下,上下兩間是樓上樓下,都在房子西盡頭,樓梯在東頭,他們都沒事。家里突然連著死了兩人,棺材是老家賬房雇了船送回鄉的。還沒辦喪事,他父母都病了。體育場原是校場的消息是他妹妹的婆家傳來的。他妹妹打來電話,知道父母病了,特來看望。開上晚飯,父母都不想吃。他妹妹不放心,陪了一夜。他的侄兒不肯睡挪入爺爺奶奶屋的小床,一定要睡爺爺的大床。他睡爺爺腳頭,夢里老說話。他妹妹和爹媽那晚都聽見家里鬧鬼了。他們屋里沒敢關電燈。妹妹睡她媽媽腳頭。到天亮,他家立即雇了船,收拾了細軟逃回鄉下。他們搬入新居,不過七八天吧,和我們同席吃飯而住在新居的五個人,死了兩個,病了兩個,不知那個淘氣的胖侄兒病了沒有。這位同學是謹小慎微的好學生,連黨課《三民主義》都不敢逃學的,他不會撒謊胡說。
我自己家是很開明的,連灶神都不供。我家蘇州的新屋落成,灶上照例有“灶君菩薩”的神龕。年終糖瓜祭灶,把灶神送上天了。過幾天是“接灶”日。我爸爸說: “不接了。”爸爸認為灶神相當于“打小報告”的小人,吃了人家的糖瓜,就說人家好話。這種神,送走了正好,還接他回來干嗎?家里男女傭人聽說灶神不接了,都駭然。可是“老爺”
相關閱讀:
- 中國檢科院制定措施援助四川質監系統 (laurie_dly, 2008-8-04)
- 氣候集團發表報告稱:中國倡導“綠色革命” (laurie_dly, 2008-8-05)
- 唐克麗研究員獲世界水保協會“杰出研究者獎” (laurie_dly, 2008-8-06)
- 外國記者和外國觀眾盛贊沈陽賽區的中國檢驗檢疫 (laurie_dly, 2008-8-18)
- 一杯滄海(吳稼祥著) (aa_tang, 2008-8-18)
- 中國全小腸移植手術取得重大突破 進入世界前列 (laurie_dly, 2008-8-21)
- 【轉帖】中國人缺少什么? (aa_tang, 2008-8-31)
- 【轉帖】學術研究的承擔 (aa_tang, 2008-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