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講壇走到政壇的平民部長周生賢:我不怕丟官
在工作上要當一把劍,為科學發展保駕護航;對待人民群眾我愿意做一頭牛,為他們耕田種地;對環保系統的這些環保工作者,我愿意做一把傘,為他們擋風遮雨。周生賢如是說。
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局長、黨組書記周生賢。(資料圖片)
周生賢出身平民,從寧夏大羅山腳下的一位中學老師,一路走到正部級崗位。
《小康》記者,遠赴千里之外的西海固,并專訪了周生賢,探尋他從中學老師到國家環保總局局長之間的歷程。
從大羅山出發
同心縣,位于寧夏自治區中部,地處六盤山系北麓。1936年紅軍長征到同心,在這兒實現了紅軍三大主力的會師。周生賢就出生在同心縣東部的韋州古鎮舊莊村。
周家一共7個孩子,兩男五女,周生賢是長子,排行老三。周家原住在百余公里外的金積鎮,因生活貧困解放前逃荒到韋州鎮。甚至到周生賢出生的時候,還沒有自己家的房子。
周的小學同學彭海強對《小康》說“小時候周生賢學習非常好,經常考第一,而且作文寫得好。”“一些學習不好的學生為了交作文,會拿白饅頭來,求周生賢替他們寫。”另一位同學回憶道。
韋州鎮回民占90%以上,所以那兒的小學都是阿拉伯語學校。小學六年周生賢學的都是阿拉伯語,到現在周仍能說一口流利的阿拉伯語(出訪摩洛哥時,周純熟的阿拉伯語,讓摩方和隨行人員都很驚訝)。
公社“挖”走老師
1965年9月周生賢考入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師范學校。1968年,師范畢業的周生賢回鄉務農,一年后作了韋州中學的老師。如果不出意外,周會在教師崗位上一直做下去。
78歲的老人楊兆岐,時任公社書記,向《小康》講述了周生賢被發現的經過。當時楊看到一份韋州中學的工作總結報告,發現這篇文章寫得非常好。于是就調查是誰寫的,調查發現是周生賢(此時周還常在《吳忠日報》、《寧夏日報》發文章),于是公社決定把這個人“挖”過來。“但是工作了幾個月,我們發現,周生賢不僅文章寫得好,工作能力還特別強,工作方法有一套,能解決基層問題。于是沒半年又提了公社副主任。”
兩年后,周從副主任的位置調任下馬關公社黨委書記。公社距毛烏素沙地南緣只有幾十公里。上任后,周就承擔了國家林業部的 “防風固沙樣板林” 項目。
“當時我們搞了154條林帶,1000多公里。中間是楊樹和柳樹兩行,這叫‘楊柳沖天起’,兩旁是沙柳,‘沙柳補空隙’,下面植草,‘雜草苜蓿拔地起’。”周生賢對《小康》談起當年的植樹工作,依然興奮。
憑借自己的鉆研以及同仁們的共同實踐,樣板林取得了成功,成了西北地區的樣板。周還被林業部安排在人民大會堂介紹了經驗。“當時的林業部長羅玉川,接見了我,跟我照了一張相,激勵了我前半生,但是我當時絕沒有想到我會成為羅玉川的接班人,這個我沒敢想。”
口碑的力量
回顧周生賢在寧夏走過的路,楊兆岐老人給《小康》總結道:“周生賢在韋州是文章好,工作方法好,能解決基層問題;在下馬關是林業搞得好;在西吉是民族工作做得好。”
當記者問到“為什么老百姓跟周生賢有這么深的交情?”楊兆岐說:“那是他為老百姓做了很多實事。”
1995年春夏大旱襲擊了西海固地區,當地建設“集雨節灌”工程,時任自治區副主席的周生賢將工作思路概括成簡短易記的口訣,“深掏井,多打窖,節水灌,九字傳,千古鑒”,“修梯田、打井窖、鋪地膜,九字不忘,脫貧有望”。采訪中《小康》記者發現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記得這口訣。
離開西吉縣的時候,周生賢怕影響群眾,決定早晨五點鐘離開,而那時天還不亮。可是剛剛四點多,周就被外面的聲音吵醒了。起來一看發現院子外面已經是擠滿了人,街上也擠滿了人,老百姓手里舉著自己做的標語,有歡送周的,也有挽留的。
同樣的場面也發生在同心縣。1984年周生賢考上了中央黨校的研究生,離開同心去上學時,路也是被老百姓圍得水泄不通。
1999年,原本傳聞要到西藏任職的周生賢被一紙調令,調到了北京。此前,組織部門已找過時任寧夏回族自治區常務副主席的周生賢,周隨后也做好了赴西藏的準備。時隔不久,西吉縣忽然發生大規模械斗事件,作過西吉縣委書記的周被派往一線去解決問題。在上級的指導下,憑借多年的群眾基礎和威信,以及對復雜問題的把握,周生賢很快制止了械斗,平息了事態,隨后被調到北京。
寧夏一位官員回憶說“周生賢走的時候,場面很感人。好幾千老百姓開著手扶拖拉機啊,農用三輪車啊,早早就趕到機場去等著送周主席去了。”群眾到了,說明了情況,擠進了機場,最后把飛機圍得水泄不通,飛機也因此晚點40多分鐘。
2003年7月的一天上午,位于和平里東街的國家林業局門前人頭攢動,80多位頭戴白色小帽的回族同胞圍聚在大門前,用當地語言與林業局傳達室的同志說著什么,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激動和興奮之情。他們乘汽車再轉火車從寧夏千里迢迢來到這里只為看一個令他們驕傲的家鄉人――在國家林業局任局長的周生賢。周生賢當時正在開會,一聽說這個情況,也很激動,他立即接待了這些也是他日思夜想的家鄉人。家鄉人還是那么樸實,并沒有因為他進京做了官就這事那事的求他來了,什么事也沒有,就一個目的,看他來了。
推動林業“拐點”的實現
“中國林業的歷史性轉變”,這是周生賢一本書的名字,但也是周生賢在國家林業局局長任上完成的一件事情。
1999年2月,周生賢調任國家林業局副局長。林業局的前身林業部在1998年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被降格,隨后又說要升格,于是周生賢被調了過來。雖然最后林業局沒有變成“林業部”。但周生賢說:“我在這個位置上干得挺愉快。”
周到了林業局后,遇到部門定位的轉變――砍樹歷史被終結,資源保護、生態建設成為首要任務。2000年11月,周生賢出任國家林業局局長。一個月后,他就向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遞交調研報告,提出將原有的十幾個林業重點工程整合為六項工程,并逐步形成以這六項工程為中心的中國林業生產力布局。這六項工程就是后來中央9號文件所寫的“新世紀六大林業重點工程”:包括天然林資源保護、退耕還林等。以六大工程實施為主要標志,周生賢宣布,我國林業實現了“歷史性轉變”――從以木材生產為主到以生態建設為主。
2006年6月公布的第三次全國荒漠化和沙化監測結果表明,56年來全國土地沙化首次實現了逆轉――由上世紀末年均擴展3436平方公里轉變為目前年均縮減1283平方公里。胡錦濤總書記特別肯定這是“非常可喜的事情”。
2005年12月8日,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和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張力軍(后排右二)一起視察佳木斯市松花江污染監測斷面。(段松君 鄧佳)
松花江不會忘記
2005年11月30日時任國家林業局局長的周生賢接到通知,到中組部候命。“在接到通知之前,我還在著手準備召開全國林業廳局長會議……說心里話,我對林業是很有感情的。但是我覺得在這個關鍵的時候,國家的需要是第一位的。我雖然感到任環保總局局長有很大的壓力,但對此我有信心。”他堅定地表示。
2005年12月1日,中央剛剛宣布任命,周生賢便出席國務院防治松花江污染會議,然后到林業局交接工作。上任第四天,席不暇暖,5日下午六點半他已經趕赴冰天雪地的東北松花江畔佳木斯市。環保總局一位處長表示,“甚至還沒有見到周生賢的面,”他“就去現場了”。
到了佳木斯,他堅持要到監測點去實地察看。佳木斯分布著3個監測斷面,相距60公里。陪同他的當地領導說:“看一個就行了吧?”周說:“不行,3個都要看。”到了江堤上,環保部門的人說:“冰薄,路滑,站在這里能看見。”他說:“站在這里看不清啊!”趟著積雪,沿著浮橋,他到江中心察看每一個取樣點,與那里的每一位工作人員握手,詢問每一個細節:多長時間取一次樣,什么時候會加大取樣頻率,穿的衣服能不能抗風寒。
在此期間,“前線”和總局的工作兩不誤,周生賢安排兩位副局長分別在黑龍江和北京協助工作。在前線,他組織制定了松花江污染防控“三步走”的戰略部署,隨后召開新聞發布會增信釋疑,引導輿論,為老百姓趕制喜聞樂見的年畫……
佳木斯市環保局局長葛鳳嶺向《小康》回憶到,周在佳木斯的大多數時間里,都是工作到后半夜兩點鐘,每天要工作十七、八個小時,到后期顯得很疲倦。面對緊張的工作局面,他著急上火,嘴上起了大泡,當周離開佳木斯的時候還沒有痊愈。
在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得到有效防控后,周生賢說:“松花江是當地的母親河,要愛護她,利用她。這次松花江環境污染的教訓,是切膚之痛,震驚了世界。要引以為戒,警鐘長鳴。”
履新環保總局下猛藥
此前海外媒體曾把中國的環保局,列為世界上最尷尬的四個部門之一,暗諷部門對自身職能履行上的尷尬。周生賢對此也深有了解,他曾毫不隱諱地指出,環保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實質,就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增長。
上任伊始,周生賢即施以猛藥,推行了一系列果斷措施。12月8日,在檢查佳木斯一些企業排污情況時,周生賢對隨行的環境監察人員說:“我們環保的權威從何而來?就是通過嚴格執法,來樹立環保部門的權威。”當日他簽署就任后的第一個緊急通知,決定在全國開展環境安全大檢查;隨后,環總局連續否決七個大項目;其后,又叫停11家對飲用水造成嚴重污染的企業,查處了10家大型違法項目……
在2006年4月18日召開的全國環保廳局長會議上,周生賢透露,以前在林業局,晚上十二點后一般沒有電話。而到環保局后,一個晚上甚至四五個電話。環保總局局長這個位置上的工作之繁忙,可見一斑。
2006年5月,周生賢嚴厲批評了當前存在的破壞環境的開發行為。他明確表示,要實現十一五規劃的環保目標,必須堅決做到不欠新賬、多還舊賬,而關鍵就在于把好“環評”這個重要關口。
周生賢還在環保系統內部推行環保官員問責制。并公布各省需要完成的環保指標,地方環保官員乃至政府官員完不成就不能提拔,顯示新一輪的環保問責風暴正在展開。
“不廉潔的事情堅決不能干”
據同心縣的一位干部回憶,周生賢一心撲在工作上,對自己的位置一直不關心。當時任命周為同心縣委書記的時候,周還在百余里外的紅寺堡植樹造林。周當時的職務是同心縣副縣長,在造林時,有位朋友打電話來說,縣委書記這個位置批下來了,上面說由你來擔任。回憶此事,周說當時覺得這是朋友在跟自己開玩笑,因為按照報上去的名單,怎么也不會是自己。于是繼續在一線指揮造林播種。結果第二天早上組織上就到縣里宣布了任命結果,縣委書記周生賢。這回接到組織電話的周生賢才從一線趕回縣里。這也被一些人戲稱說:“周生賢植樹,回來就能當縣委書記。”
談到這件事情,周說:“我最討厭跑官要官了,現在的一些年輕人把官位看得太重了。”“凡是到我這兒來跑官要官的,肯定無法得逞。”
記者來到周出生的地方,一個用泥坯圍起來的院子里面蓋了幾間房子。周的弟弟周生輝還住在這里,他現在鎮上作紀委書記,但自己還在種地,跟當地的農民沒什么區別。
據記者了解,周的弟弟當年軍隊轉業回來成了民辦教師,轉正的需要考試,結果只差1.5分。而當時周生賢就作同心縣的縣委書記,弟弟找到他,他卻死活不肯幫忙。弟弟只能自己努力,第二年考的成績很好。
當地的一位干部說:“周部長也不提拔提拔他弟弟,這么多年了還在鄉里。稍微說句話至少也該作個縣領導了吧?”以至于當地很多人說周生賢有點不近人情。
《小康》記者看到舊莊村雖然離鎮上不遠,但是基本上沒有自來水。一位當地的干部說:“前幾年鎮上安自來水,自來水到他家只有一二百米的時候,想修過去。但周的父親堅決不讓按,說大部分人還沒有安自來水,咱們也不能搞特殊。”
快要離開韋州的時候,隨行的一位干部偷偷告訴記者說“周的父親去世不能下葬本村,他家也沒說什么話,也沒有找縣里領導。”因為當地的風俗,漢民不能在本村下葬。但是這個時候,周已經是部級領導了。“只要說一聲,縣里肯定會把這些問題解決好。但是周家就是沒有跟縣里說。”
家庭讓我放心
周生輝還記得, 1969年前后,剛畢業回來的周生賢經人介紹娶了鄰村的姑娘,下雨的天氣,用驢車把新娘子拉回來了,簡短的儀式,就算婚禮了。
談起自己的家庭,周說:“家里這方面情況還是算不錯的”。“孩子也都比較爭氣,家庭除了老伴全家都是研究生,一半是博士,我的三個孩子,都結婚了,還有一個小孫子。”
“我跟我們老伴也是有分工,家里的事我不管,單位的事她不管。我現在拿多少錢我都不知道。我們家里的這些開支,一切都由老伴說了算。我們定這個規矩的時候家里的大事她問我,但是我這結婚幾十年從來沒有過大事,也沒有問過我,都是她在那兒開支。”
采訪中《小康》了解到,除了不準夫人參政。周也明令禁止秘書把自己的電話和家庭住址告訴其他人,特別是想來辦事的。
同心縣的一位老同志回憶, 80年代前后周的妻子是同心縣某工廠工會的領導之一,當時按照規定在領導崗位上的工人可以轉為干部。按照正常程序報到縣委后,結果時任同心縣委書記的周生賢首先就把自己妻子從名冊中拿下。以后在西吉和到銀川后,也有很多機會,但是周生賢始終不同意。以致他妻子最后退休的時候身份仍然是工人。
“(因為子女)品行都比較棒,自己都有自己的事業,家庭現在非常和諧,所以這樣反過來就增添我的信心。下午,如果我們談到五點多,老伴就要來電話,問我今天下午吃什么飯了。”周生賢說。
國家環保總局局長周生賢。(資料圖片)
對話——周生賢:我不怕丟官
2005年12月1日,周生賢臨危受命成了國家環保總局局長。他如何盤點自己一年多的為政得失?如今他又承受著怎樣的壓力?
前不久,周生賢在他的辦公室接受了《小康》雜志的獨家專訪。
《小康》:您希望環保總局在民眾心目中是什么形象呢?
周生賢:環保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真正列入議事日程,所以流傳著這樣一個話,“環保嘛,就是宣傳起家,收費養家”;國內說我們是“三澀部門”,就是地位苦澀,關系青澀,囊中羞澀。
而我在調查研究的過程當中,發現環保是伴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調查的結論是,一部環境保護的歷史,就是一部正確處理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關系史,所以環境問題必須跟經濟結合考慮,環境問題才能列入應有的議事日程。
我當時就認為,搞好環境保護的“牛鼻子”就是正確處理經濟增長跟環境保護的關系,后來我就圍繞這個問題做調查研究,給中央建言獻策。在這個調查研究基礎上,中央開了第六次環境保護大會, “制定了新時期環保工作的部署”。環保資金從2006年開始,特別是從2007年開始相對有大幅度的增加。雖然時間非常短,但在很大程度上環保進入了一個、扮演了一個從綜合部門進入宏觀決策部門的角色,改變了前面那種尷尬的局面。
通過這些年的工作,我們正逐步改變在全國人民心目中的環保工作形象。
《小康》:這一年多來您覺得最遺憾的事情是什么?
周生賢:最遺憾的是我們的約束性指標“沒降反升”。
中央把GDP作為預期性的指標,而把能源和環保這兩個指標——單位GDP節能20%,污染總量控制減少10%,作為約束性指標。
2006年國家環保總局應急中心共處置環境事件159起,是2005年的兩倍。但這一年執行的結果,約束性指標不但沒有降下來,反而升了。這是不是我們的工作部署有問題呢?你看中央花這么大的力氣,我們也是把吃奶的勁都用上了,迎來的就是“不降反升”,所以這既是我遺憾的一件事情,也是壓力最大的一件事情。
《小康》:您是從基層老師、公社書記做起的,您覺得基層的經驗給您帶來什么樣的影響?
周生賢:一方面,我在省里干了30年,在北京干了10年,過去30年我是向上看了30年,從下面向上看,調到北京以后我是從上面向下看,有好多問題才清楚。回過頭來這樣一看,過去有些事可以不那樣干,也可以做得更好一些。
另一方面,回過頭來看我們現在制定方針政策毛病也比較多,為什么執行的時候有些東西落實不下去,因為執行政策的過程當中,結合實際方面還有差距,所以現在我們不能簡單的說,哎,我們現在都是抓落實不夠,一個是抓落實不夠,難道都抓落實不夠嗎?所以在政策制定過程的當中出現了問題,這樣“一上一下”才看清楚了。
《小康》:您怎么看講真話跟官位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你怎么處理?
周生賢:如果你把當官作為一個工作和為人民做事的一種條件,而不是一種可以追求的東西,你就會當的很輕松。你比如講“不降反升”,我并不怕我丟官,我甘心在丟的時候,丟的活該,丟了我也高興,但更重要的咱要把這個事情做好,我不是說指標“光降不升”,和2005年相比,2006年的二氧化硫、化學需氧量排放增幅分別下降了11.3%和4.4%,應該說成績不小,可我更多地是考慮中國的環境狀況必須要改善和提高。
《小康》:2006年4月,第六次全國環保大會上溫家寶總理強調,做好新形勢下的環保工作,關鍵是要加快實現三個轉變。您如何看這三個轉變?
周生賢:三個轉變是歷史性的、戰略性的、方向性的。總理講話時全國近12萬人聽了報告,用電視電話的形式傳下去,全世界為此發了兩萬多條新聞,評總理這三個轉變的思想。
所以這個思想提出來以后,應該說成為中國環境保護的一個里程碑。所以我們就根據三個轉變的思想,制定或調整了現有的不符合三個轉變思想的一些法律法規,補充了一些規章。盡管現在做得遠遠不夠,按我們的設計是三到五年清理完畢,現在應該說已經有了良好的開端。中國人說的好,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所以我現在對此還是非常有信心。
《小康》:據我們所知,環保總局曾利用2個月的時間進行機關思想作風整頓,您怎么看待當前有些部門的機關作風問題?
周生賢:機關整頓的目標是有限的。主要是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先進性教育整改不到位的問題,群眾意見很大;第二個就是部分干部對“三個轉變”不適應的問題。當時機關整頓的時候,先進性教育給大家承諾的東西有些沒有兌現,比如說住房問題,幾百戶人沒有房住。有一套房子,爭得頭破血流,這種問題特別突出,等等,都需要通過整頓來改善和加強。現在回過頭來看,整頓達到了預期目的,基層的同志普遍反映總局的作風有了明顯改進。機關的同志工作勁頭也更足了,心氣更順了。
《小康》:您當林業局長時在中國林科院上了兩年的研究生班,到了環保總局有什么打算?
周生賢:在林業局當局長時,開始的時候我幾乎連什么是林分都搞不清楚,心里很著急。這樣怎么能勝任工作,怎么與專家學者在同一平臺交流?于是我痛下決心,利用節假日和休息時間到中國林科院研究生班上課,一直堅持了兩年。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到環保局工作,這也是我最不熟悉的一個行業。所以現在我又在中國環科院進行學習,我加入他們的研究生班。我是去年的元月7號進去的,到現在已整整一年。記得那天是2007年元月8號,正是一個學期結束放假的日子,校長說,局長,從下一周開始放寒假,你可以不來了,開學的時候再來。我說好,他們說局長,我說這個不是局長,全都是你的學生,都應按學校的制度辦。
《小康》:《中國林業的歷史性轉變》一書出來在國內國際均產生巨大影響。很難想象這本書是利用節假日寫出來的。您如何看自己的這部專著?
周生賢:這個書沒有一個人給我幫忙,我不會打字,我都是寫出來的,讓他們去打。所以這個書要有藝術的語言概括,就是把真誠獻給人民,發自內心的,對中國林業的熱愛。
《小康》:但現在很多官員因為沒有時間去學習,也沒有時間寫書。
周生賢:一天擠出來半個小時讀書,你一年就可以讀好多書,我就不信誰連半個小時都擠不出來。
《小康》:那您怎么看待學習呢?
周生賢:首先有一個認識問題,你為什么要學習?你學習干嘛呀?我的目的很明確,我學習是為了彌補自己專業知識的不足,不是為了圖虛名,搞學歷。我是工作當中遇到問題解決不了、影響決策才學。比如污水治理這個東西不清楚,你不可能有正確的決策,這就是我學習的目的。記得當初在中國林科院研究生班畢業的時候,中國林科院要授予我博士學位,我堅決不接受。學習要能堅持下去,學習要有三股勁:第一,讀懂弄通靠鉆勁,這也是我的經驗;第二,長期堅持靠韌勁,我認為地方官就應該講地方話,所以我在寧夏就講寧夏話,到了北京也講北京普通話。我開始來北京的時候,念一個文件要出一身汗,現在可以了;第三就是獲得時間靠擠勁,時間就像海綿里的水,只要你擠它總是有的。
-
政策法規

-
標準

-
焦點事件

-
焦點事件

-
焦點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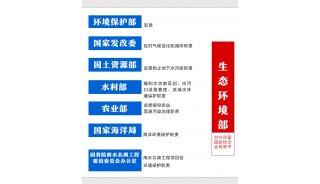
-
焦點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