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銘賢:用實驗說話是科學公認的一個重要特征
最近,國際上不斷有干細胞應用研究的進展傳來,例如,用干細胞治療心臟病、腦部疾病等。其中,對我觸動最大的還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一項研究。據報道,該校醫學研究中心科學家利用實驗鼠胚胎干細胞取代受損視網膜細胞,成功地幫助患色素性視網膜炎的實驗鼠恢復了視力,有望開發出治療人類色素性視網膜炎的新方法。同時,他們也坦陳有些實驗鼠出現了良性腫瘤和視網膜脫離的并發癥。真要應用于人類,仍需進一步探索。
我早就聽說,我國一些醫院在干細胞治療中曾意外地發現個別盲人恢復了視力,“重見光明”。這一“奇跡”廣為傳播,甚至上了美國的電視。按理說這是一個很好的“苗子”或線索,深入追究下去,有可能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拔得頭籌。遺憾的是,一些醫生和科研人員陶醉在“奇跡”之中,津津樂道于宣揚乃至夸大療效,而未能拿起科學實驗的利器,至今還不清楚是什么干細胞起作用,如何起作用,為什么起作用,有何副作用等關鍵問題,更談不上推廣應用了。據國外媒體消息,我國某些機構用干細胞治療病人多達五六千人,卻未見一篇發表在學術期刊上的論文。
這是我們的一根軟肋。必須正視這根軟肋。
愛因斯坦在談到近代科學的興起和發展時,曾多次明確指出“系統的實驗”是決定性條件之一。確實,沒有伽利略和牛頓的科學實驗,談何近代科學?我們上中學時讀到巴甫洛夫致科學青年的信,不會忘記他強調事實是科學的土壤和空氣的教誨。這里講的事實,指的便是科學實驗的事實,如他在創立條件反射學說時著名的狗搖鈴喂食實驗。用實驗說話是科學公認的一個重要特征。
具體至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同樣要建立在科學實驗的堅實基礎上。作為關于人體試驗的最基本的指導文件,《赫爾辛基宣言》從1964年制訂到2008年修訂,都一再堅持“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必須遵循普遍接受的科學原則,必須以對科學文獻及其他有關信息的全面了解為基礎,以充分的實驗室和動物實驗為基礎”。通常說,臨床應用要以臨床前研究和臨床實驗為前提,所依據的正是這一普遍接受的科學原則。《赫爾辛基宣言》還規定,在治療病人的過程中,當不存在經過證明的干預措施或這些干預措施無效時,可以使用未經證明的干預,“可能時,應該對該項干預進行研究,旨在評價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目前,大多數干細胞治療還屬于“未經證明的干預”,非常需要用科學實驗來證實,完善或否證。
既然如此,那為什么不用實驗來說話呢?我想,原因不外乎下述兩點:
其一,難。科學實驗歷來難,于今尤甚。自然界是那樣的紛繁復雜,而且如達爾文所言,喜歡說謊話,把假象呈現在人們面前,要揭開其廬山真面目,當然大不易。幾百年來,科學實驗說了那么多話,破解了自然界那么多奧秘,要繼續深入下去,登上新的高峰,當然更難。就以干細胞來說吧,有胚胎干細胞、成體干細胞,還有人工誘導的多功能干細胞(ips)。干細胞最神奇也最被看重的是它具有自我更新和多向分化的特性,然而,正是這一特性又注定了它很不確定、難以控制,真要通過實驗說點真話、新話,談何容易?
其二,利。按照生命倫理規范,人體試驗研究必須征得受試者的知情同意,而且不能向受試者收費,倘若發生與試驗相關的傷害還要給受試者合理補償。顯而易見,用實驗說話和廣招患者、直接治療相比,從短期的可見的效益看,不啻相差十萬八千里。在市場經濟下,誰不追名逐利?誰會干“賠了夫人又折兵”的傻事?
不過,不用實驗說話,勢必得不出經得起檢驗的科學理論,因而也不可能得到科學界和公眾的首肯,不管一時多么自鳴得意,多么財源廣進,終究不可能真正占領干細胞應用的高地。比如,用干細胞治療色素性視網膜炎等眼疾,美國很可能走在我們前面。到時候說不定還要去購買人家的專利,受制于人。誰愿意出現這種局面?因此,不管多么困難,不管一時可能損失多少收益,都要下決心組織精兵強將,給予足夠的財力物力支持,選擇若干合適的項目,開展臨床前研究和臨床試驗研究,爭取在干細胞的應用研究中取得更多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重大成果。
在這方面,其實我們有榜樣可效仿。中科院動物所研究員周琪與上海科學家曾凡一等合作,用實驗證實了ips的全能性。活潑可愛的ips小鼠(“小小”)的驚艷問世,立即傳遍全球,成為亮麗的科學明星,被國際權威媒體《時代周刊》評為2009年十大醫學進展之一。最近,周琪又與王秀杰等合作,發現位于小鼠12號染色體上的決定干細胞多能性表達水平的關鍵基因簇,進一步推進了對ips的認識,也有利于ips的臨床應用,可見,用實驗說話真可謂價值連城,與急功近利者追逐的小利根本不可同日而語,中科院副院長施爾畏倡導“崇尚實踐、勇于創新、追求價值”的文化,我舉雙手贊成,但愿這篇短文能成為它一個不起眼的注釋。
-
科技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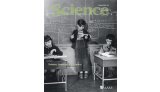
-
焦點事件

-
科技前沿

-
科技前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