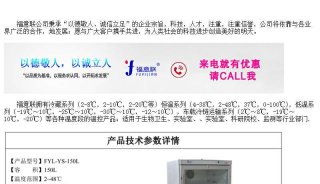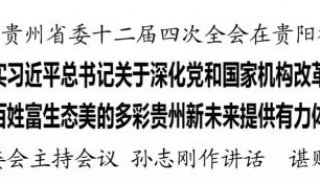機構改革后,如何保護“保護地”

王朗自然保護區。徐衛華供圖
中國是生物多樣性的一片沃土,約占地球陸地面積6%的廣袤土地上,有濕潤的熱帶森林,有一望無垠的平原草場,也有巍峨險峻的冰川雪山,千里冰封的永久性冰原……這里擁有全世界15%的脊椎動物和12%的植物物種。
但同其他任何國家一樣,中國也面臨著保護生物多樣性的艱巨挑戰。在2018年大刀闊斧的政府機構改革后,這項事業迎來了一片新局面。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主任歐陽志云團隊系統分析了政府機構改革給中國自然保護地建設帶來的機遇,提出了一系列完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建議,相關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生態學領域頂級期刊《生態與進化趨勢》(Trends in Ecology & Evolution)上。
九龍治水,混亂在所難免
中國共有約1.2萬個自然保護地,其中嚴格意義上的自然保護區有2700多個(截至2017年),總面積約147萬平方公里。
除此之外,中國還建立了許多其他類型和名稱的自然保護地,諸如森林公園、風景名勝區、地質公園等,這些自然保護地的面積通常都比較小。
論文指出,占中國國土面積20%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卻長期面臨一個核心問題:交叉重疊的管理模式。某一個具體的自然保護地,往往由一個以上不同的政府部門或機構管轄。這些實體機構會根據各自不同的職責權限,為保護地制定不同的規劃目標和管理規則。以海南省為例,118個陸域和濱海保護地中,至少有50個存在部分的行政管理重疊,其中自然保護區、森林公園和風景名勝區的行政重疊程度最大。
“這種‘九龍治’的模式,導致了一系列問題。”論文通訊作者歐陽志云說。
首先是難以對全國的自然保護地開展統一規劃。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系統設計和全面規劃,我國現有的自然保護地體系與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重點區域不相匹配。比如,我國的自然保護地多集中在西部,尤其是青藏高原地區。而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的許多關鍵區域分布在中國的東部或南部,這些區域的保護地建設嚴重不足。
其次,不同自然保護地的保護與管理目標不一致,甚至相互沖突。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濕地公園、地質公園、水源地保護區、社區保護地……盡管名目繁多,但這些區域卻常常有著相似的功能,特別是旅游、娛樂等能直接帶來經濟回報的功能。相比之下,生態保護等公益性的功能卻很容易被遺忘。
1978年,原林業部將九寨溝作為國家級大熊貓自然保護區管理。自1982年起,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也將其列為國家風景名勝區。2004年,這里又成為國家地質公園,承擔原國土資源部的地質景觀保護任務。
如此,這片土地就被賦予了至少三個名字,由三個不同的政府部門管理。
“盡管是同一批行政人員在實施具體管理,但不同類型保護地的管理目標之間卻難免發生沖突。當保護與發展發生沖突時,管理部門往往選擇后者。”歐陽志云對《中國科學報》說。而蓬勃的旅游業在帶來顯著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很可能影響物種保護效果。
根據原國家林業局發布的全國大熊貓調查報告,從1988年到2013年間,該保護區的大熊貓數量有所減少,而周邊其他山脈大熊貓的數量卻在增加。
最后,是自然保護地分類體系與國際接軌的問題。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根據主要管理目標將自然保護地分為6類:嚴格自然保護區、原野保護地、國家公園、自然紀念物、棲息地/物種管理區、陸地/海洋景觀保護地和資源保護地——每一類都有明確的保護目標和配套標準。
“而中國雖然有不同的保護區級別和類型,但目前這些分類體系都不能體現管理目標、檢查標準和管理方式上的差別。”中科院動物研究所副研究員解焱曾撰文指出。
三江并流,如何依法治理?
在云南省的西北山區,金沙江、瀾滄江和怒江三條大江并行奔流,山高谷深、雪峰皚皚,遍布珍禽異獸——這里是中國三大物種多樣性中心之一,也是世界級的物種基因庫。
1989年.這里被列為國家風景名勝區,2003年又進入了世界自然遺產名錄。不僅如此,這里還先后建立了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地質公園、森林公園……不同的牌子之下,空間重疊很大,卻遵從著不同的管理規定。在很多情況下,這些管理規定不僅互相矛盾,甚至還會互相抵消。
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保護區管理條例》禁止在核心區和緩沖區進行開發或商業活動,而《風景名勝區管理條例》則沒有禁止放牧、伐木、狩獵等可能影響物種保護的活動。盡管這些活動會導致物種棲息地隔離和野生動物棲息地的退化。
“令人遺憾的是,即使這個地區的生態環境退化,我們也很難向責任方追責,因為導致后果的決策,恰恰是符合相關類型保護地管理規定的。”論文第一作者、中科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研究員徐衛華對《中國科學報》說。
“哪個部門應該對什么事情負責?保護地的管理績效應如何體現?誰該受到懲罰或獎勵?”歐陽志云說,“在這些問題沒有得到很好回答的情況下,管理就難以有效,問責就難以實現。”
機構改革,抓住嶄新機遇
2018年3月以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開展了大刀闊斧的政府機構改革,正部級機構減少8個,副部級機構減少7個,部分部門合并或隸屬于上級機關。
“這是一個契機。”徐衛華說,“一些與自然保護密切相關的改革將有利于我國重新建立統一、規范、有效的自然保護地管理體系——管理機構越少,目標和職責越一致,就越能減少職能重疊或沖突。”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所有國有自然資源和資產的所有權從多個部門轉移到了一個新成立的部門:自然資源部。自然資源部在制定國土空間規劃,包括保護地規劃時,有權同時考慮開發和保護目標。
“這種變化,有助于解決過去‘九龍治水’導致的空間重疊、缺乏協調以及管理目標和規則相互沖突等問題。”歐陽志云說。
這次改革還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地方。比如自然資源部管理的新機構——國家公園管理局,將負責我國正在進行的國家公園改革以及所有自然保護地的統一管理。
一旦國家公園建立,所在范圍內原先由不同部門管理的其他自然保護地將被廢除,其他區域交叉重疊的各類保護地也將按照一定規則整合為一個保護地,實現一個保護地、一塊牌子、一個管理機構。
原生態環境部經過一系列調整后,已不再具體管理自然資源和自然保護區,只負責督察各類保護地的管理工作,這就完成了“運動員”和“裁判員”的分離,將有助于更加客觀地評估和監管保護區。
新成立的生態環境部也大有可為。2018年9月,生態環境部對7個自然保護區的不當管理做出了迅速反應,責成有關地方政府解決自然保護區內非法資源開發問題。
“盡管政府機構改革必然會對我國保護地建設與管理帶來顯著改觀,但有幾個問題仍值得注意。”歐陽志云說。他們在論文中也提出了一系列建議:重新構建自然保護地分類體系,建議在國家最新提出的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和自然公園的基礎上,考慮建立生態功能保護區,以便與生態保護紅線相協調;綜合考慮珍稀瀕危物種、自然生態系統、自然景觀和自然遺跡,編制統一的自然保護地體系規劃;構建統一的自然保護地法律體系。
“政府機構改革開啟了我國自然保護領域的歷史性變革。近來涌現的一批相關研究,對如何借助這一歷史契機,構建統一、規范、科學、高效的自然保護地管理體制,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參考意見。”
未參與此項研究的國家林業和草原局調查規劃設計院副院長、國家公園管理辦公室副主任唐小平說,“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層面從體制上理順了全國自然保護地統一管理問題的同時,許多基層卻出于精簡機構數量等原因,撤銷了負責保護地管理職責的林業部門,合并了自然保護地專業管理機構,取消了保護地執法力量,這實際上嚴重削弱了自然保護地的管理能力。希望未來能有更多研究者和決策者關注基層實踐的問題。”
論文鏈接:https://doi.org/10.1016/j.tree.2019.05.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