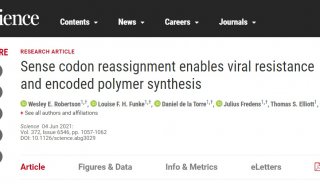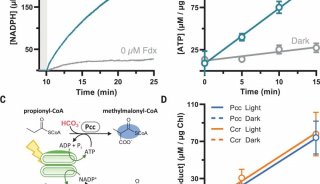生命難造
3月21日,一篇發表在美國《科學》雜志上的論文引起轟動:美國生物學家克雷格·文特爾花了15年時間、4000萬美金,利用化學手段合成一種 DNA,并將其注入一個被“挖空”了的細胞,制造出一個新的生命體“辛西婭”。
“首例人造生命誕生”這一新聞引起公眾的爭議甚至恐懼。但事實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出現所謂“人造生命”;最近三年至少已有兩次類似的新聞。
2007年,來自日本和法國的一個科學家小組宣布造出“人造細胞”。其實,他們在實驗室里得到的是一種人造細胞膜,也就是細胞的框架。“人造細胞膜”與真正的細胞膜結構相似,具有蛋白質合成功能。
2008年9月,哈佛大學的科學家報道說他們即將合成生命,主要是指他們建立了一種單細胞模型,該模型算得上是一種新的“生命”形態。事實上,他們可能只是人工合成了一部分核苷酸,僅僅是實現簡單遺傳基因序列的復制。
從技術上看,這次“人造生命”與前面幾次還是有區別的。文特爾突破了如何讓人造基因序列生成人造染色體的難點,而人造染色體的形成,意味著一個物種遺傳密碼的完備,意味著真正生命體的誕生。
英國《自然》雜志邀請了幾位不同專業領域的科學家發表評價和意見。美國佛羅里達州應用分子進化基金會的斯蒂芬·伯納認為,根據現存各個物種的基因組序列,人們可以推斷出這些物種已滅絕的祖先的基因組,再依據文特爾等人的工作,就可以合成出那些已滅絕的古老生物——這些古老生物將會告訴我們100萬年前地球的生態環境。
而賓州大學的生物倫理學家亞瑟·卡普蘭說,研究成果可以徹底平息有關生命到底需不需要特殊力量才能被創造和生存下來的爭論,甚至可以顛覆人類長久以來對于生命本質的看法。
但也有另一種聲音。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的生物技術與生物工程教授馬丁·福斯內哲認為,人造細胞的誕生只是證明了一種技術上的進步,并不算觀念上的突破——嵌合生物早已通過育種被制造出來了,最近,將基因轉移到去核的靶細胞中也培育出了嵌合生物。
和1997年首個克隆哺乳動物多利羊的誕生相比,“人造生命”的誕生所面對的評論已經有了很大不同。
當年,人們在驚嘆克隆技術的同時,大多數人都在攻擊克隆技術可能帶來的生物倫理方面的問題,這種爭論持續了很多年,尤其是當有人提到要克隆人類的時候。而現在,面對“人造生命”,無論是普通民眾還是科學家,包括美國總統奧巴馬,都要求評估此事件可能帶來的風險,以及如何能以最小的風險獲得此成果所能夠帶來的利益。
科學家提出了這項技術可能引發的一些問題,比如有人可能會拿這項技術去研制生物武器、人造生命可能會改變地球原有生命系統的結構,出現人類不可控的情況等等。但生物學界的觀察家們還是贊同開放這門科學,原因是:若病原體能通過電腦設計出來,那么,防治的疫苗同樣也能如法炮制。
多利在6歲多的時候就死了,對于它的“早衰”和死亡,在一個從事生物學和醫學工作的科研人員看來,生命還是應該按照他固有的模式進行繁衍、孕育,按照正常的、已經延續了萬萬年的規律,從受精、胚胎形成,到母體中孕育,再到出生,經歷成長的整個過程,直至最后的死亡。
而對于這個剛剛從實驗室生產出來的“人造生命體”,其實不應把它當做生命,只能把它當做一個產品——它是靠幾瓶化學物質和計算機生產出來的一種類似生命的產品。
人類可以制造一個簡單的生命體,但是人類還沒有強大到了解生命調控的各個環節,從制造一個簡單的生命體、一個細胞,到能夠制造出一個完整的植物或動物,甚至于人,生命本身還有很多秘密是我們迄今不知道或者不了解的。人造生命的時代并未真正到來,所有的人應該尊重生命,更要尊重生命的本質。
本文作者為中國科學院華大方瑞司法物證鑒定中心主任、生物學博士
-
科技前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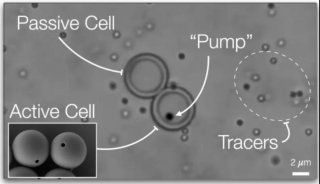
-
科技前沿

-
科技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