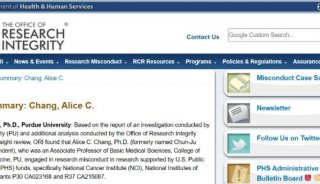發表論文“集團作案”,底線不可觸碰!
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別多——這兩年學術論文造假也玩出了新高度:自去年開始,幾大主要的學術論文出版社紛紛大幅度發布撤稿通知,成百篇論文因為“同行評審造假”而被撤稿。
同行評審是什么,300多年就一直以來都是確保學術論文質量的一道金標準,除了能保證原創論文的科學性,創新性之外,同行評審也是剔除粗糙和錯誤的研究結果和論點的一道底線。而自去年被發現的一系列造假事件涉及到了這一底線,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造假行為方式多樣化,比如論文作者提前讓朋友提供正面評價,精心設計同行評審圈,圈子里的評審人相互評價各自的論文,模仿真是的評審人,甚至捏造完全不存在的評審人。
此次涉及國內論文的不少是學術“大咖”,這也是第一次大規模出現中國學術論文撤稿。
這種同行評審造假已經形成“集團作案”,據稱這些作者之間沒有明顯的關聯,但是推薦評審人相似,因此值得懷疑可能存在第三方機構進行暗箱操作。
這就單是中國學術界的問題嗎?
當然這不僅是中國學術界的問題,此前BMC科研誠信部副主任Jigisha Patel就曾表示,這并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來自中國的論文總數量本來就比較多,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而愛思唯爾出版全球總裁Philippe Terheggen也表示,首先相較于論文發表量的增長,撤稿量其實并沒有相應增加,而且發表文章數量最多的國家,撤稿的數量也最多。因此像某些媒體指出的中國論文都不靠譜的以偏概全的命題并不準確。
但今年Springer,愛思唯爾兩大出版集團曝出撤稿問題所涉及的出處,確實很大一部分都來自于中國,而且一直以來代寫論文,代投論文的論文“一條龍”服務灰色產業鏈也給公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學術論文出現大規模被撤稿,我們本身的問題占主要原因。
底線為何一退再退?
從偽造數據,竄改圖表內容,到代寫代發學術論文,再到今天的偽造同行評審,學術造假的“規格”越來越高,底線一退再退,也越來越難以偵破察覺。我們的這些學術圈里“聰明人”的心思都花在了學術造假上,難道他們就真的不怕懲戒嗎?
說起來他們可能真的不怕,目前大多采用的是行政處分,去除職務等等,那么讓我們來翻一翻法律法規:“偽造數據”這一違規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計量法》中提到過,但一般只用于質量技術監督系統,比如稅務、房產等方面,其中提及的是“使用不合格劑量器具或破壞計量器具準確度和偽造數據”,而這所涉及的懲罰也僅為2000元以下的罰款。
另外從抄襲的角度來看,雖然根據我國的著作權法,抄襲他人作品需要承擔一定的民事責任,但很少有人會提出起訴,這主要是因為一般論文抄襲,協商解決的較多,走民事訴訟途徑不一定能取得好的結果。
那么刑法懲戒呢?其實早在2005年就有政協委員提出,“對嚴重剽竊行為應該追究刑事責任,在刑法中設立‘剽竊罪’,制裁學術腐敗。”2012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閆希軍也曾建議加強學術誠信的法制化管理,他認為,應當盡快把遏制學術不端行為納入立法體系。通過立法,明確學術行為人的權利與義務關系,使學術誠信的要求能夠標準化和可操作。通過立法,建立健全對學術不端行為的投訴舉報機制,形成完善的外部監督。與此同時,加強執法監督,加大對學術不端行為的懲處力度。
就此韓國“黃禹錫事件”是一個很好的對照,當時韓國首爾地方檢察廳介入調查,最終以欺詐罪、挪用公款罪以及違犯《生命倫理法》的罪名起訴黃禹錫,黃禹錫被判2年徒刑,緩刑3年。據《經濟導報》報道,這主要是因為這一事件涉及了大量科研經費的使用問題。
其實國內也有類似的例子,就在去年,國家審計署在對十多個工程和應用研究大型項目進行調查后,發現了5所大學的7名教授涉嫌濫用國家科技重大專項資金2500多萬。陳英旭、宋茂強2人被依法判刑;李寧、李澎濤、王新月、王甫4人被依法批捕。李寧是第一個牽涉貪污案件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其有可能成為被剝奪院士頭銜的第一人。
未來如何加強論文審閱?
各大出版社都針對同行評審造假問題提出了新的對應措施,比如愛思唯爾計劃開發作者推薦同行評審人郵箱驗證系統,Springer也表示打算更仔細地對同行評議人員推薦進行嚴格核實。在未來它下屬的期刊有可能會要求提供研究機構的e-mail地址或是審稿人的Scopus作者編碼(Scopus author IDs)。
一些出版商例如BioMed Central和PLoS,已經響應偽造同行評審這一問題終止作者推薦審稿人這種做法,他們的計劃是采取一些“不那么極端”的措施,例如復核審稿人的非機構e-mail地址,將使得一些期刊能夠保留住這些評審人提供的專業意見。
-
焦點事件

-
焦點事件

-
焦點事件

-
焦點事件

-
政策法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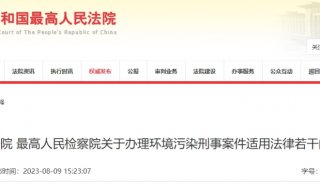
-
焦點事件

-
焦點事件

-
焦點事件

-
焦點事件

-
焦點事件

-
焦點事件

-
焦點事件